古代医德名言篇(一)
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黄帝内经》
论曰: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候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 东汉?张仲景《伤寒论》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北宋?范仲淹《能改斋漫录?卷十三》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枪,勿避险峻,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工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是谓得道。《黄帝内经》
受病有浅深,使药有重轻。度其浅深,分毫不可差;明其轻重,锱铢不可偏。浅深轻重之间,医者之精粗,病者之性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得失之间,死生性命之所系,医之道不得不为之难也宋?史堪《史载之方》
夫用药如用刑.误即便隔死生。盖人命一死不可复生,故须如此详谨,用药亦然。庸下之流,孟浪乱施汤剂,逡巡便至危殆,如此杀人,何太容易?清?年希尧《本草类方》 人身疾苦,与我无异,凡来召请,急去无迟,可止求药,宜即发付,勿问贵贱,勿择贫富,专以救人为心。 宋?张杲《医说》
欲救人而学医则可,欲谋利而学医则不可。清?费伯雄《医方论》
医以苏人之困,拯人之危,性命为重,功利为轻,而可稍存嫉妒哉?奈何今之医者,气量狭窄,道不求精,见有一神其技者则妒之。妒心一起,害不胜言,或谣言百出,或背地道破道,或前用凉药,不分寒热而改热,前用热药,不别寒热而改凉,不顾他人之性命,惟逞自己之私心,总欲使有道者道晦,道行者不行,以遂其嫉妒之意。清?雷丰《时病论》 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 晋?杨泉《物理论》
凡有请召,不以昼夜寒暑远近亲疏,富贵贫贱,闻命即赴。视彼之疾,举切吾身,药必用真,财无过望,推诚拯救,勿惮其劳,冥冥之中,自有神佑。 元?曾世荣《活幼心书》
凡为医者,遇有请召,不择高下远近必赴。宋?《小儿卫生总微方论》 凡病家请看,当以病势缓急,为赴诊之先后。病势急者,先赴诊之;病势缓者,后赴诊之。勿以富贵贫贱,而诊视便有先后之分。清?冯兆张《冯氏娜囊秘录》 夫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说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虽余曰病易速救,要须临事不惑,唯当审谛覃思,不得于性命之上。率尔自逞俊快,邀射名誉,甚不仁矣! 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偶然治瘥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育也。所以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于冥运道中,自感多福者耳。又不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令彼难求,自炫功能,谅非忠恕之道。志存救济,故亦曲碎论之,学者不可耻言之鄙俚也。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夫医道者,以济世为良,以愈疾为善。盖济世者凭乎术,愈疾者仗乎法,故法之与术,悉出《内经》之玄机,此经固不可力而求,智而得也。金?刘完素《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
古代医德名言(二)医者诊脉,不识寸关,放手妄言虚实。不问得病之由,今经几日,是表是里,曾无传染,只据所见,便言某证。证且未的,不顾汗下次第,或病人劳复,便毁前医为误,甚至子谈父过者有之,弟掩兄长者有之。及其治疗,本无所长,原其所以,则志在于利。医人乘急取财者,甚于盗贼。 元?王珪《泰定养生主论》
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清?喻嘉言《医门法律》
医道,古称仙道也,原为活人,今世之医,多不知此义,每于富者用心,贫者忽略,此故世者之恒情,殆非仁术也。以余论之,医乃生死所寄,责任匪轻,岂可因其贫富而我之厚薄?告我同志者当以太上好生之德为心,慎勿论贫富,均是活人,亦是阴功。明?龚廷贤《万病回春》
不可过取重索,但当听其所酬。如病家赤贫,一毫不取,尤见其仁且廉也。 明?李梃《医学入门》
医为人命所关。人之所系,莫大乎生死。王公大人,圣贤豪杰,可以旋转乾坤,而不能保无疾病之患。一有疾病,不得不听之医者,而生杀唯命矣。夫一人系天下之重,而天下所
系之人,其命又悬于医者,下而一国一家所系之人更无论矣,其任不亦重乎。清?徐大椿《医学源流论》
?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其立德也;挽回造化,立起沉疴,此其立功也;阐发蕴奥,聿著方书,此其立言也。一艺而三善咸备,医道之有关于世,岂不重且大耶!?清?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华序》
夫医为仁道,况授受相传,原系一体同道,虽有毫末之差,彼此亦当护庇,慎勿訾毁。斯不失忠厚之心也。明?龚廷贤《万病回春》
?盖医之为道,所以续斯人之命,而与天地生生之德不可一朝泯也。?元?王好古《此事难知?序》
?医道微也,非绝欲无私,通神于微妙之乡,穷理尽性,研几于幽明之极者,不足以传也。?清?王士雄《潜斋医话?医鉴》
?凡作医师,宜先虚怀,灵知空洞,本无一物;苟执我见,便与物对;我见坚固,势必轻人,我是人非,与境角立,一灵空窍,动为所塞,虽日亲近人,终不获益,白首故吾,良可悲矣。?明?缪希雍《本草经疏?祝医五则》
?凡作医师,宜先虚怀,灵知空洞,本无一物;苟执我见,便与物对;我见坚固,势必轻人,我是人非,与境角立,一灵空窍,动为所塞,虽日亲近人,终不获益,白首故吾,良可悲矣。?明?缪希雍《本草经疏?祝医五则》
?学不贯今古,识不通天人,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宁耕田织布取衣食耳,断不可作医以误世!医,故神圣之业,非后世读书未成,生计未就,择术而居之具也。是必慧有夙因,念有专习,穷致天人之理,精思竭虑于古今之书,而后可言医。?明?裴一中《言医?序》 ?世徒知通三才者为儒,而不知不通三才之理者,更不可言医。医也者,非从经史百家探其源流,则勿能广其识;非参老庄之要,则勿能神其用;非彻三藏真谛,则勿能究其奥。?清?柯琴《伤寒来苏集?季序》
凡乡井同道之士,不可轻侮傲慢。与人切要谦和谨慎,年尊者恭敬之,有学者师事之,骄傲者逊让之,不及者荐拔之。如此自无谤怨,信和为贵也。 明?陈实功《外科正宗》 行医之要,惟存心救人,小心敬慎 ? 若欺世询人,止知求利,乱投重剂,一或有误,无从挽回。病者纵不知,我心何忍?清?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
明医箴:今之明医,心存仁义;博览群书,精通道艺。洞晓阴阳,明知运气.药辨温凉,脉分表里。治用补泻,病审虚实;因病制方,对症投剂。妙法在心,活变不滞;不炫虚名,
想找一些中国四大名医的名言警句!
关键词:明清时期;辨证论治;脏腑辨证;脏腑病机
摘要:脏腑辨证之说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明清时期脏腑辨证之说似乎少有医家提倡,但脏腑辨证之法却被广泛地应用。其面貌特点的改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脏腑辨证与多种辨证方法相融互参,成为多种辨证方法的基础。2.对肾、命门、脾胃、肺、肝等病机认识愈加深入、病证分型愈加完备。3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从注重哲理思辩到重视具体应用的转折。该时期是脏腑辨证的推广应用时期。
脏腑辨证之说历经了秦汉时期的理论奠基、晋唐时期的成长、宋元时期的成熟,它在明清时期又呈现了怎样的发展特点呢?归纳起来,特点有三。
“脏腑辨证”一法融入辨证众法之中
明清时期,除江涵暾著《笔花医镜》(公元1834年,道光十四年),将脏腑辨证之说作了简要总结外,已少有医家将脏腑作为疾病分证的首要纲领而独立提倡。该时期随着辨证论治思想的逐步确立,各种辨证方法层出不穷,如辨八纲、辨卫气营血、辨三焦、辨络脉等。而上述诸种辨证又无不关乎脏腑,所谓万变不离其宗,表明脏腑辨证之法已广泛地融入其他辨证方法之中,辨脏腑是其他诸种辨证的基础。
1.脏腑辨证与“八纲”互参
历各时期,医家倡导脏腑辨证多从“虚实寒热”来分型,明清之际仍然提倡脏腑辨证说的《笔花医镜》更是以脏腑统“八纲”:“按对病情,审为何脏何腑,是阴是阳,不乖乎表里虚实寒热之真,即知为心肝脾胃肺肾之疾”[1]。由于“阴阳之分,总不离乎表里虚实寒热六字尽之。夫里为阴,表为阳,虚为阴,实为阳,寒为阴,热为阳”[2],故各脏腑病症从表里虚实寒热六个方面分型。不仅如此,江氏明确了脏腑虚证、实证还有气血痰郁之别。比如“心之虚,血不足也”,“心之实,其症为气滞、为血痛,为停饮,为痰迷”。而此前的《医学启源》对于考试大/网站收集脏腑气血痰郁的证型还没有明确表述,仅能够从其治法“补血”、“补气”、“通滞”、“除湿”等间接反映。
明清众医家逐步确立了察病辨“八纲”的辨证论治思想。其中明张景岳的“二纲六变”辨证体系即是后世八纲辨证的原型,但亦不离脏腑,以“八纲”统脏腑。张氏将“审阴阳”作为辨证的总纲,即“二纲”,辨“表里寒热虚实”为其次,名为“六变”[3]。“六变”之下皆要辨脏腑。如“辨虚实”包含辨五脏虚证、五脏实证:“辨寒热”含有辨五脏寒证、五脏热证。据考这些脏腑分证的内容主要源自独重脏腑辨证的《中藏经》。同时,认为凡里证皆应定位于五脏:“里证者,病之在内在脏也。”[4]
2.卫气营血及三焦辨证以脏腑为基础
明清医家在温病领域创立卫气营血及三焦辨证论治体系。卫气营血及三焦辨证不仅包含了脏腑辨证,而且以脏腑辨证为理论基础。首先,叶天士创立的卫气营血辨证把人体从表到里或由浅入深分为卫、气、营、血四个层次,反映病位与病性的轻重情况和传变情况。其中以卫代表肺与皮毛,气代表肺、胸膈、脾、胃、肠、胆,营代表心与心包,血代表肝、肾。叶派传人吴瑭创立三焦辨证论治体系,把人体躯干分为上焦、中焦、下焦三部分,以反映疾病重心所在及传变规律,上焦包括肺与心,中焦则包括脾与胃,下焦包括肝与肾。所以辨证最终要落脚于脏腑。
3.络病辨证亦究脏腑
清代是络病理论发展的鼎盛时期,尤其以叶天士的“久病入络”说为代表,集大成于《临证指南医案》,丰富了《内》、《难》关于络病辨证的内容。络病辨证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辨脏腑,病在某之络,便有某脏之症。在病证上《叶案》中记有“肝络凝瘀”、“胆络血滞”、“伤及肝脾之络,致血败瘀留”之腹痛、“瘀血积于胃络”之胃脘痛,有“吸入温邪,鼻通肺络,逆传心包络中”之温热病,有“阴风湿晦于脾络”之中风等。病久必及阳明胃络,叶氏继承《内经》的相关理论,以调治脾胃络脉功能作为治疗脾胃疾病的重要原则。胃病治络当辨新久气血。可总结出八种辨证:气郁络中、热入胃络、痰饮阻络、胃络瘀结、胃络虚寒、胃络气虚、络燥失润、络血不足。总之对络病的辨证在明辨所属脏腑的同时详辨其虚、实、寒、热、风、湿、痰饮、血瘀等不同证型。尤其关于脏腑络病虚证的诊治是对《内经》的重要补充。
4.奇经辨证责于肝肾
叶天士还发挥了奇经辨证。奇经为病多与肝肾久损有关,他说:“医当分经别络,肝肾下病,必留连及奇经八脉,不知此旨,宜乎无功”。[5]见有奇经八脉失司不固的病证,强调以调补肝肾为总的治法,多选用血肉有情之品填补奇经,还认为八脉为病的证治不离肝肾,亦牵涉阳明脾胃。他总结道:“凡冲气攻痛,从背而上者,系督脉主病,治在少阴;从腹而上者,治在厥阴,系冲脉主病,或培补阳明”。[6]
脏腑病机新论迭出
明清医学,其理论内容及范式是金元医学的延续。而研讨脏腑病机及诊治正是这两个时期医学传承的主题。河间学派,其研究的六气病机或火热病证皆以脏腑为基础。该学派的影响经“丹溪之学”绵延至明清两代,如戴思恭、王履、王纶、虞抟、汪机。易水学派更是以张元素为首倡脏腑议病,众弟子究脏腑病机以继之,他们对明代温补派医家影响极大。在金元医学影响下,明清各家,继续深入探讨脏腑病机及诊治,已是人言言殊。
1.肾命新识
明代温补派医家们深入阐发了肾命在人体生理病理中的关键作用,并将其运用于内伤杂病的诊治。薛己继承了东垣补脾、钱乙益肾之长,注重肾与命门,视其阴阳虚实之偏颇而论治,还强调肾命对脾胃的温煦作用。在其影响下明以后诸医家逐步将肾命的探索引向深化。赵养葵倡“命门”新说,否定了自《难经》以来左肾右命的观点,认为命门五行属火,位在两肾中间,命火养于肾水,二者既须分又不可截然而分,而命门处于主导地位。命门是君主之官,五脏的生机都根源于命门之火。同时倡导命门说的尚有张介宾、孙一奎,他们的认识大同小异。唯张介宾强调命门水火、阴阳互根,而且认识到真阴为生命的物质基础,显然比单纯的命门相火论和命门元气论又有所提高。李中梓遥承易水之绪,仍以兼顾脾肾为说,谓先天之本在肾,后天之本在脾,在证治中贯穿了先后天根本的学术思想,认为精血之源头在乎肾,阳气之源头在于脾,因此虚劳治疗亦重在脾肾。
2.对肺的认识
与明代温补派医家强调脾肾命门不同,明·绮石开始强调肺在虚损病证中的作用,对虚劳病证强调肺阴虚证治。认为劳嗽、吐血、骨蒸、尸疰等阴虚成劳之证,皆统于肺,立清金保肺法。其对肺阴虚证治的发挥,于以往在虚损病证上只着眼于脾肾二脏而言,无疑更为完备了。
喻昌在其“秋燥论”中联系肺的病理、证候特点阐述了肺燥证。他认为秋伤于燥,燥则伤肺,《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说“诸气(月贲)郁,皆属于肺;诸痿喘呕,皆属于上”是指(月贲)郁、诸痿、喘呕等病证皆由燥气过胜,耗伤肺津,清肃之令不能下行而致。治疗主以甘柔滋润之药,并制定清燥救肺汤。其对肺燥证治的发挥,不但是对《内经》的新的诠释,更丰富了关于肺的辨证内容。
另外,明·张景岳还述及今之所谓肺阳虚证[7]、清·薛生白所论“肺胃不和”[8]等证无不丰富了对肺的认识。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
3.对肝的认识
自朱丹溪阐发郁证以来,明清医家更为重视木郁之证,赵养葵在《医贯》的郁病论中提出辨证治疗从肝入手,解决了木郁,则其他疾病迎刃而解;林佩琴在《类证治裁》中认为凡病多起于郁,气候变化如气运乖和,则五郁之病生;情志拂郁,则六郁之病作。诸病多从肝来。何梦瑶在《医碥》中说:“百病皆生于郁……郁而不舒,则皆肝木之病矣”。[9]张锡纯提出人之元气根基于肾而萌芽于肝,凡元气之上脱、精之下夺、汗之外泄,均由肝虚所致。很多医家更扩大了肝病范围。魏之琇的《续名医类案》一半以上病例涉及情志,尤以怒气为多。傅青主以肝统治内、妇科病,治肝法贯穿其女科全书。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卷首即设中风、肝风、眩晕、头风、虚劳等与肝相关之病,书中所载风、劳、臌、膈四大重证无不与肝相涉。该时期肝病辨证之精细,则以王旭高为最。王氏认识到“肝病最杂,而治法最广”而将其分为肝气证治、肝风证治、肝火证治三类。肝气证治,又分肝气旺中气虚、肝气乘脾、肝气乘胃、肝气上冲心、肝气上冲肺。肝风证治又分为阳亢、血虚、中土虚不能植木、中土虚寒导致虚风。肝火证治分为上逆、炽张、伤阴侮金、水不涵木。根据阴阳气血虚实寒热的不同,制定补肝、镇肝、敛肝、散肝、平肝、搜肝等治肝三十法。
4.脾胃新说
明·缪希雍阐发脾阴证治,纠正了前人专主温补脾阳之一偏。诊断脾阴不足,缪氏归纳出“脾元虚”与“内热津液少”两大要点;提出以“甘寒滋润”为补益脾阴之法。滋阴大法从元末的主用苦寒到缪氏主用甘寒是一个重要转折。这对叶天士尤有重要影响。
叶桂强调脾胃分论,创立胃阴学说。胃属阳土,宜通,喜柔润;脾属阴土,宜藏,喜刚燥。因此,脾阳不足,胃有寒湿,宜温燥升运,用东垣之法;若见阳盛之体,或患燥热之证,或病后伤肺胃之津液,以致虚痞不食,舌绛咽干,烦渴不寐,肌燥高热,便不通爽,主以降胃之法,用玉竹、花粉、沙参、石斛、麦冬等甘平或甘凉濡润之品养胃阴,使津液来复而通降自成。其脾胃分论、胃阴宜养的观点给后学以很大启发。此后的医家对脾或脾胃的阴虚证逐渐重视起来。
除上述外,具体到某种疾病的脏腑辨证也日见丰富,如中风、泄泻、血证等。比如出血病证,张介宾认为“当察五脏”,张石顽主张“须辨脏腑”,并在病机、表现上都作了总结。唐宗海论血证尤其系统地阐发了脏腑病机,如“肺,主行制节,故五脏六腑,皆润利而气不亢。肺中常有津液,润养其金,故金清义伏,若津液伤,则口渴气喘,痈痿咳嗽。金不制木,则肝火旺,火盛刑金,则蒸热喘咳,吐血劳瘵并作。”[10]
汪昂出生于哪里
十一、经络针灸
1. 善用针者,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2. 头者,诸阳之会。(宋·陈言《三因极-病证方论·头痛证论》)
3. 肚腹三里留,腰背委中求,头项寻列缺,面口合谷收。(明徐凤《针灸大全·四总穴歌》)
4. 治痿者,独取阳明。(《素问·痿论》)
十四、治则治法
1. 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未乱。(《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2. 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3. 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4. 其高者,因而越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5. 其下者,引而竭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6. 中满者,泻之于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7. 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8. 其在皮者,汗而发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9. 其慓悍者,按而收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10. 其实者,散而泻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11. 有余者泻之,不足者补之。(《素问·疟论》)
12. 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素问·至真要大论》)
13. 温者清之,清者温之。(《素问·至真要大论》)
14. 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素问·至真要大论》)
15. 燥者润之,急者缓之。(《素问·至真要大论》)
16. 坚者耎之,脆者坚之。(《素问·至真要大论》)
17. 衰者补之,强者泻之。(《素问·至真要大论》)
18. 踈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素问·至真要大论》)
25. 微者逆之,甚者从之。(《素问·至真要大论》)
26. 坚者削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素问·至真要大论》)
27. 结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滞之。(《素问·至真要大论》)
28. 急者缓之,散者收之。(《素问·至真要大论》)
29. 损者温之,逸者行之。惊者平之。(《素问·至真要大论》)
30. 热因寒用,寒因热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素问·至真要大论》)
31. 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汉·张机《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
32. 治病必求其本。(《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33. 实则泻之,虚则补之。(《素问·三部九候论》)
34. 盛者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灵枢·经脉》)
35. 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素问·至真要大论》)
36. 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明·张介宾《类经·标本类》)
37. 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素问·六元正纪大论》)
38. 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明·李中梓《医宗必读·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论》)
39. 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清·吴瑭《温病条辨·治病法论》)
40. 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清·吴瑭《温病条辨·治病法论》)
41. 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清·吴瑭《温病条辨·治病法论》)
42. 瘀血不去,新血不生。(清·唐宗海《血证论·吐血》)
43. 发表不远热,攻里不远寒。(《素问·六元正纪大论》)
44. 体若燔炭,汗出而散。(《素问·生气通天论》)
45. 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46. 热*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寒,以酸收之,以苦发之。(《素问·至真要大论》)
十五、药物方剂
1. 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素问·至真要大论》)
2. 补汤宜用熟,泻药不嫌生。(明·傅仁宇《审视瑶函·用药生熟各宜论》)
3. 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素问·宣明五气篇》)
4. 半夏有三禁,渴家汗家血家是也。(明·缪希雍《先醒斋医学广笔·春温夏热病大法》)
5. 附子无姜不热。(清·黄宫绣《本草求真·干姜》)
6. 石膏非大剂则无效。(清·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伤寒兼有伏热证》)
7. 一味丹参饮,功同四物汤。(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丹参》)
十六、临床疾病
1. 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素问·咳论》)
2. 治咳嗽者,治痰为先;治痰者,下气为上。(金·张元素《活法机要·咳嗽证》)
3. 喘病之因,在肺为实,在肾为虚。(清·叶桂《临证指南医案·喘》)
4. 哮以声响名,喘以气息言。(明·虞抟《医学正传·哮喘》)
5. 无痰不作眩。(元·朱震亨《丹溪必法·头眩》)
6. 无虚不能作眩,当以治虚为主。(明·张介宾《景岳全书·眩晕》)
7. 诸有水肿者,腰以下肿,当利小便;腰以上肿,当发汗乃愈。(汉·张机《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
8. 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汉·张机《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
9. 稠浊者为痰,清稀者为饮。(明·李中梓《医宗必读·痰饮》)
10. 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明·李中梓《医宗必读·痰饮》)
11. 盗汗为阴虚,自汗为阳虚。(清·江涵暾《笔花医镜·盗汗自汗》)
12. 胃不和则卧不安。(《素问·逆调论》)
13. 蛔得酸则静,得辛则伏,得苦则下
1、疔疮先出血,内毒以寒泻.
2、眩晕者无痰不作,消渴者无火不生.
3、肥人眩晕少气多痰,瘦人眩晕少血多火.
4、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5、痢无补法。
6、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
7、养阴不在血,而在津与汗。
8、疹是太阴风热。
9、癍是阳明火毒。
10、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
11、巅顶之上,唯风可到。
12、温病凭脉伤寒凭症。
13、其在皮者,汗而发之。
14、初病在经,久病在络。
15、不懂何经何络,开口动手便错。
16、金水相生,子盗母气。
17、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18、亢则害,承乃制。
19、暴聋属实,久聋属虚。
20、欲求南风,先开北窗。
21、肠痈下不厌早,肠癖补不厌迟.
22、上焦如羽,非轻不举.
23、无水舟停,增水行舟。
24、风为百病之长,头为诸阳之会。
24、阳虚则外寒,阴盛则内寒。
25、人身不过表里,气血不过虚实。
26、通邪三法汗、吐、下。
27、寒*于内,治宜甘热。
28、热*于内,治宜咸寒。
29、面肿为风,脚肿为水。
30、导龙入海,引火归渊(源)。
31、苔黄腻热在肝胆,苔黄燥热在脾胃。
32、月满勿补,月亏勿泻。
33、肝胆之症,以下为主。
34、清肝必须降火,清心必须豁痰。
35、病不辨则无以治,治不辨则无以痊。
36、去邪而不犯无过之地。
37、克敌者存乎将,去邪者赖乎正。
38、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
39、法不过仲景,理不过内经。
40、培之以黄芪,燥之以白术,补气健脾何患不除。
41、外入之寒,温必兼散,内生之寒温必兼补。
42、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
43、宁舍其穴,不舍其经。
44、渴喜饮冷,腹中有热,渴喜饮热,腹中有寒。
45、所为邪者,从亏而见。
46、湿热毒火,首见肝经。
47、阳络伤则吐血,阴络伤则便血。
48、五脏之伤,穷必及肾。
49、大毒治病十去其六,中毒治病十去其八。
50、上燥治气,中燥增液,下燥治血。
51、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方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到血直须凉血散血。
52、内热曰烦,外热曰燥。
53、寒之不寒无水也,热之不热无火也。
54、留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
55、火动风生热筋挛脉急,风扇火炽,而炽乱神迷,外窜经脉则成痉。
56、实则谵语,虚则郑声。
57、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
58、火郁发之,木郁达之,金郁泄之,土郁夺之,水郁折之。
59、营行脉中,卫行脉外。
60、膏粱之变,足生大丁。
61、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
62、孤阴不生,独阳不长。
63、阳虚恶寒,阴虚恶热。
64、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
65、胃本不呕,胆木克之则呕。
66、升降出入,无器不有。
67、形寒饮冷伤肺。
68、木扣金鸣,土中泻木。
69、耳聋宣肺。
70、胃喜清凉,脾喜温。
71、胀在腹中痞在心下,胀有形,痞无形。
72、一切气病用气药不效,少佐芎归血气流通而愈。
73、水精四布,五经并行。
74、中气实则病在阳明,中气虚则病在太阴。
75、少阳属肾,肾上连肺。
76、淋属肝胆,泻属脾胃。
77、人身无倒上之痰,天下无逆流之水,故不治痰而治气。
78、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
79、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
80、足太阴痰厥头疼非半夏不能疗,眼黑头眩虚风内作非天麻不能除。
81、内不坚则善病风。
82、伤于风者上先受之,伤于湿者下先受之。
83、辛开苦降,芳香开窍,淡渗利湿。
84、脉络空虚贼邪不泄。
85、脑为元神之府,心为藏神之脏。
86、阴平阳泌精神乃滞。
87、手心热来腹中热,手心凉来腹中凉。
88、发热恶寒者发于阳。
89、无热恶寒者发于阴。
90、恶寒非寒明是热症。
91、恶热非热明是虚症。
92、久病非寒,暴病非热。
93、久痛无寒,暴痛无热。
94、麻是气虚,木是血虚。
95、牙痛长,腿痛短。
96、冬不用栀子,夏不用麻黄。
97、久病多瘀,怪病多痰。
98、从阳化热,从阴化寒。
99、有一分恶寒,便有一分表证。
100、久病必瘀,久病必虚。
101、急则治标,缓则治本。
102、虚则补其母,实则泄其子。
103、扎针拔火罐,病好一大半。
104、中药不效,炮制不到。
105、四季脾旺不受邪。
106、肝阳上亢,水不涵木。
107、气症饮水,血症不饮水。
108、热在上焦,气伤则渴。
109、热在下焦,血伤则不渴。
110、血之为病,上焦瘀血小便必难,下焦瘀血小便必自利。
111、一切血症,日轻夜重,一切气症,日重夜轻。
112、一切火症,心急潮热,一切水症,胁硬心下怔忡。
113、无阳则厥,无阴则呕。
114、凡病昼则增剧,夜则安静,是阳病有余及气病血不病。
115、凡病夜则增剧,昼则安静,是阴病有余及血病气不病。
116、昼则发热,夜则安静,是阳气自旺于阳分也。
117、夜则恶寒,昼则安静,是阴血自旺于阴分也。
118、昼则安静,夜则发热、烦躁,是阳气下陷于阴中也。名曰:热如血室。
119、夜则安静,昼则恶寒,是阴气上溢于阳中也。
120、昼则发热、烦躁,夜则发热、烦躁,是重阳无阴,急泄其阴峻补其阳。
121、昼则恶寒、夜则烦躁,饮食不入,名曰:阴阳交错者死。
122、内侵膻中则为厥。
希望对你有用!
汪昂
汪昂(1615-1694年),字_庵,初名恒,安徽休宁县城西门人,曾中秀才,因家庭贫寒,遂弃举子业,立志学医。他苦攻古代医著,结合临床实践,经过30年的探索研究。编著有《素问灵枢类纂约注》、《医方集解》、《本草备要》、《汤头歌决》等。
中文名:汪昂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安徽休宁
出生日期:1615年
逝世日期:1695年
职业:医学家中医
代表作品:《素问灵枢类纂约注》、《本草备要》、《医方集解》
个人简介
汪昂(1615-1695年),字仞庵,明末清初安徽休宁西门人氏。汪昂自幼苦读经书,“经史百家,靡不殚究”,是县里的秀才。明朝末年,汪昂寄籍浙江丽水,期间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欲走仕途,但每每名落孙山。
明朝灭亡后,随着汪昂年龄以及阅历的增长,他越来越看清科举考场的腐败,开始厌恶科举制度,又由于明亡而有感于国家民族的兴衰,于是,在清朝顺治初年,毅然弃儒学医,笃志方书,并以其毕生的精力从事医学理论研究和著书立说,从而著有大量医学科学普及书籍,盛行于世,成为一代新安医学名家。
主要贡献
汪昂诊病,注重临床。其一重脉证,二注药性。汪氏以为:医学之要,莫先于切脉,脉候不真,则虚实莫辨,攻补妄施,鲜不夭人寿命者。其次则当明药性,如病在某经当用某药,或有因此经而旁达他经者(《本草备要》自序)。
在长年的行医过程中,汪昂发现“古今方(医)书,至为繁夥”,而为医方注释之书却很少。自陈无择首创张仲景《伤寒论》注释后,“历年数日,竟未有继踵而释方书者”。给初涉医门者带来了很多的困难,医方难以掌握。于是,汪昂便广搜博采,网罗群书,精穷奥蕴,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汪昂68岁时写成《医方集解》。
《医方集解》全书六卷,分21门,共收入正方370余方,附方490余方。此书博采古书,既吸收了宋代陈无择解释仲景之书以及明代新安医家吴昆《医方考》等书之优点,又结合了自己长期的临床实践,先解释受病之由,次说明用药之意,分别宜忌,唯求义明。《医方集解》刊行之后,迅速流行全国,1935年被曹炳章先生编入《中国医学大成》,1959~1979年上海科技出版社曾先后七次刊印发行,全国中医高校将其列为参考教材,1999年国家中医药出版社再次将汪昂医学全书编入《明清名医全书大成》,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发式。
人生经历
汪昂弃儒攻医,时年三十有余,可谓大器晚成。其抛弃仕途,改而学艺,认为“诸艺之中,医为尤重”,于是乎独专医学。在没有老师的情况下,身居避远山区,全靠自身勤奋,博览群书,刻苦钻研,而终成一代名家。
主要著作
汪昂不仅擅长临证,专心研究医学理论,而且十分重视医药的相互作用,其常曰“用药如用兵”。认为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虽为完善、周明,然而过于浩繁,于是乎汪昂“特裒诸家本草,由博返约,取适用者,凡四百品,汇成小帙”,取名为《本草备要》。
《本草备要》(四卷)1683年成书,后经清代初年三大名医之一太医院判吴谦审定,1694年在国内广为刊行,总数有70余种版本之多。1729年(日本享保14年)流传日本,植村藤治郎将《本草备要》刊印并在日本发行。之后,《本草备要》翻印次数至少超过200余次之多,在当代临床类实用本草中影响最为深广。该书选药精当,重点药效突出,使用方法翔实,读之令人兴趣盎然,不仅是药物学专著,也是学习中医辨证论治、立法处方的好医书。书中记载了汪昂个人的独特见解多达120余处,例如用三文钱的中药车前子一味治愈宋代翰林学士欧阳修(文忠)的暴泻等医案案例,并在中医书籍中较先提出了人脑的功用,故而深受医界喜爱,成为中医药人员必备的学习书籍之一。
人物评价
汪昂一生诊务繁冗,然其著书立说至老不倦。他著书立足于基础,着眼于普及,并讲究实用,文字流畅,通俗易懂。汪昂一生著作丰硕,除《医方集解》、《本草备要》,尚著有《素问灵枢类纂约注》、《汤头歌诀》、《经络歌诀》、《痘科宝镜全书》、《本草易读》等书。这些著作与前人相比“皆另为体载,别开经路,以前贤为竞之旨,启后人便易之门”。
《中国医学史》称汪昂“其书浅显易明,近人多宗之”,乃为我国清代著名医学科普及启蒙派的代表人物。
主要成就
汪昂在学医过程中,深感《素问》、《灵枢》“理至渊深,包举弘博”,为医家必读之经典。然篇卷浩繁,文字古奥,病症脉候、针灸方药,错见杂出;“又随问条答,不便观览”。虽然历代有不少医家对《黄帝内经》
(包括《素问》和《灵枢经》)进行整理、编次、校订或注释,但大多内容繁杂,重点欠明,不便于掌握内容要领。他对元代滑寿于《读素问钞》中将《素问》中不同内容分12项予以摘抄的编撰法,较为赞赏,乃仿其方式,选录《素问》、《灵枢》主要内容(不包括针灸)加以条析,分为脏象、经络、病机、脉要、诊候、运气、审治、生死、杂论等9篇,酌取各家学说予以简注,编成《素问灵枢类纂约注》2卷,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序而刊行。他认为《素问》治兼诸法,文字重于说理;《灵枢》偏重于针灸、经络,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体现于术数。因此,所辑各篇原文以《素问》为主,《灵枢》为副,但对精要内涵,大致予以赅括。为了便于读者查阅,所引《内经》原文,均注明出处,不致相互参错。虽于《内经》原篇有所删节,但段落依旧,前后条贯,并无割裂原文之弊,较之滑寿《读素问钞》,别具特色。原著经过汪氏重新分类编次,增强了系统性。其中的注文多辑自唐代王冰、明代马莳、吴昆和清代张志聪等诸家研注《内经》的著述,并能结合个人学习《内经》的心得,畅抒己见。他在该书序言中谈他如何
编纂此书时说:“或节其繁芜,或辨其谬误,或畅其文义,或详其未悉,或置为阙疑。”立论多较允当,力求阐发《内经》奥旨蕴义。由于他编写过程中注意精选《内经》原文(多系学术价值较明显,或对临床具有指导意义的内容),且分类有序,注释较为语简义明,浅显扼要,故此书在《内经》节注本中颇有影响,后世甚至有将它作为《内经》教材者。以上大致反映了汪氏在医学理论方面的造诣和著述成就。
汪昂在普及本草学、方剂学著述方面,尤有突出的贡献,对后世的影响相当广泛。本草学自《神农本草经》(约成书于汉代)问世以后,历代著作相当丰富。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广收博引,论述精博、全面,载药达1892种,对本草学的研究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该书篇卷浩繁,备而不要,难以尽读,不便于初学入门。而《本草蒙筌》、《药性歌赋》等书又拘于文字对偶,阙略尚多,要而不备。再者,上述几种本草著作,只言某药治某病,而未说明主治之所以然,即或偶有解释药性者,也大多辨析不详,文字表述不够明晰、流畅,影响到本草学知识的普及。面对这种现状,汪昂决心在“备”、“要”二字上下功夫,编撰一部以介绍药性、主治为主的普及性的本草专书。他潜心研究历代本草,博采诸家学说,以李时珍《本草纲目》和明代缪希雍《本草经疏》二书为主,删繁就简,由博返约,取常用药400余种,约于康熙二十年(1681)辑成《本草备要》一书。十年后,他又增补60余种,名为《增补本草备要》,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刊行于世,但后世仍沿用旧名《本草备要》。全书共分8卷,卷首列“药性总义”一篇,概述药物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配伍、归经、功用、禁忌及炮制大要。后将470余种药物分为草部、木部、果部、谷菜部、金石水土部、禽兽部、鳞介鱼虫部和人部,分类介绍。每药先辨其气、味、形、色,次述其所入经络、功能及主治。以“十剂”宣、通、补、泻冠于首,以土产、修治、畏恶附于后,并对不少药物注明毒性、服法、饮食宜忌、采药时间、异名、功效及真伪鉴别等。另有附图400余幅。此书体裁新颖,颇具特色,选药精要,对临床最常用药物几乎赅括无遗,并且文字明晰流畅,便于记诵。
汪氏论药,注意引录本草名著精要之说予以综括。在学术观点方面,师古而不泥古,并能折衷前贤论述而多有创见。如书中既有18反、19畏之内容,又据临床实践提出异议,而不拘执于前人“相反相畏”之说;其于药性,虽列百家之言,然必参以己见,判断其曲直是非。此书虽为本草专著,为了更切于临床参考,论药之时,必参之以论证,并将药性结合病证或病因相互阐发,亦将中医之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学的理论与药物学内容熔为一炉,以辨证论治的原则贯穿始终,使读者有规可循,遣药变通有法,既明理义,又切合实用。因此,该书自刊行后流传甚广,刊本达
60余种之多,其中最早为康熙三十三年(1694)刻本,另有1729年日刻本等。由于此书论述浅显,释理明畅易懂,对普及本草学知识影响很大,
也可以说是国内第一部普及性本草名著。清代以前,历代医学家编撰的方书不少。在医方分类、方剂理论等方
面亦有所阐发,但于方解方面着力不多。金成无己《伤寒明理论》对制方之理虽有论及,但所述医方只20首。明代吴昆著《医方考》,其注解医方虽较成氏有所增加,但多限于个人识见,其方义述理或不够详明,收方范围亦欠广。汪昂认为,医者知有方,亦当知方之解。否则“执死方以治活病,其不至于误世殃人者几希?”。有鉴于此,他在撰写《本草备要》的同时,又仿照宋代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及吴昆《医方考》遗意,广收博采,集录诸家之说,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著成《医方集解》一书相辅而行,互资为用。此书共3卷,选收方剂近700首(包括正方与附方),按功能分为补养、发表、涌吐、攻里、表里、和解、理气、理血、祛风、祛寒、清暑、利湿、润燥、泻火、除痰、消导、收涩、杀虫、明目、痈疡、经产计21门。各门之首,均简要阐述其功能、适应证及主治病证的病因病机。各方名之下,简注功效及方剂出处,次列主治病证、方药组成,再次方义解释及附方加减等,并对各方所治病证的病源、脉候、脏腑、经络以及治法,无不备录。书后尚附“救急良方”一章,记载了20余种意外或暴发危证的抢救方法,以备仓猝之需。书后附《勿药元诠》1卷,以简要、流畅之笔叙,晓示读者防病养生之大要。汪昂所辑诸方,多为临床所常用的历代名方,大多属于药味精炼、药性平和,方效可靠者。其选方范围,博取于历代医书;选方宗旨,以理法精当、实用有效为原则,大多属名医创用之方,亦有出自名不见经传的医家效验之方,体现了其选方较为客观、求实的态度。书中所载述的一些后世常用名方(如百合固金汤、金锁固精丸等),由于原始文献已散佚不存,幸赖汪昂收载而得以传世。在方剂分类上,汪氏参考“十剂”说,按功能分类并予以扩充,又揉合前贤的见解,创立了将方剂学按病因和治法予以综合归纳的分类方法。这种方剂分类法较为完善,便于临床应用,并使方剂学成为一门不依附于本草学或病证学的独立学科。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同类方剂的有关内容,便于据病选方;同时也避免了同一方剂的重复出现。这不仅在当时是一个创举,对后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汪昂以后的方剂学专著(如吴仪洛《成方切用》、张秉成《成方便读》等),大多沿袭此法进行分类,甚至目前出版的《方剂学》教材,也基本沿用汪昂的医方分类法。在对待各方的方解方面,汪氏汇古今数十位医家之学术精髓,上自《内经》、《伤寒杂病论》,下迄金元四大家和明代、清初诸贤之论,均予选录,博览约取,附以己见,阐发立方蕴旨。他释方着意于“辨证论方”,“虽名方解,而病源脉候、脏腑经络、药性治法,罔不毕备”,释方与临床密切结合,从而使理、法、方、药相应贯通,为后世方书之释方树立了规范。《医方集解》由于有以上特点,问世之后,流传甚广,对后世影响很大,长期以来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成为中医门径书中之重要著作。刊本多达50余种,现存最早为康
熙二十一年(1682)刻本。
在《医方集解》刊行之后,通过10余年的实践,汪昂编撰了一部使读者能在较短时期内学习并掌握临床常用方剂的著作《汤头歌诀》,遂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刊行问世。此书选常用方剂300余首,编成流畅易读的七言歌诀200余首,并在每方之下附有简注,以补方歌因音韵限制或过简之不足。汪氏此编的特点在于粗分门类(按功能分20门,类似《集解》),便于检索;且“歌不限方,方不限句;药味药引,俱令周明;?并示古人用药触类旁通之妙,便于取裁”。此书受到初学者的欢迎,流传甚广,对后世方剂学之教与学有很大影响。刊本达30余种之多。后人多有仿此体例而编写方歌,或予续补,或改编,或增注,或作白话解,多不胜数。至今学习中医者,尚多以此书作为入门读物。
汪昂的治学观点较为纯正、客观,他既重视阐扬《内经》等经典医籍之蕴旨,对汉唐以降之方药著作及临床名著亦均所探究,还善于接受新的科学知识。明末清初,西方医学随传教士渐入我国,汪昂对此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他认为西医虽不明气化之理,但对人体形态方面的论述较为确凿;并认为前贤所说“脑为元神之府”、“灵机记忆在脑”之说亦颇可取。他在《本草备要》辛夷条下说:“吾乡金正希先生尝语余曰:人之记性,皆在脑中。?昂思今人每记忆往事,必闭目上瞪而思索之,此即凝神于脑之意也。“汪昂在学术思想上崇古而不泥古,乐于接受西方医学知识,即医不分中西,当择善而从,对后世之“中西汇通派”在学术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此外,汪昂对养生学亦颇有研究。他所编撰之《勿药元诠》、《寿人经》等养生学著作,简要介绍历代养生要言,并阐述导引、气功、摄养等防病健身方法和对一些常见疾病的预防,以及饮食、起居等方面应注意的问题。汪昂从壮年业医至耄耋之年,精勤不倦,矢志普及,著述不息,在
《本草备要》自序中可以明确地看到署有“休宁八十老人”字样。“利物利人”、“有禅世道”是汪昂一生追求的目标。他立志以医济
世拯疾,为祖国医学的继承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难能可贵的是,汪昂为古代名医中自学成才的医药学家,谦虚好学,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他在《医方集解》凡例中说:“余不业岐黄,又学无师授,寡见鲜闻,尤称固陋,安能尽洞古人立方之本意哉。”这种谦虚、求实的态度,值得大家学习。汪昂的主要贡献,体现于他丰富的医学著述,除上述多种外,另有《脉诀歌》等手著,总计近10种之多。汪氏的学术影响及其对后世学习医药方剂学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屈指可数的重要人物。
本文来自作者[沛芹]投稿,不代表葡萄号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zputao.com/pu/5293.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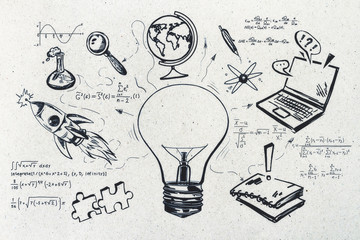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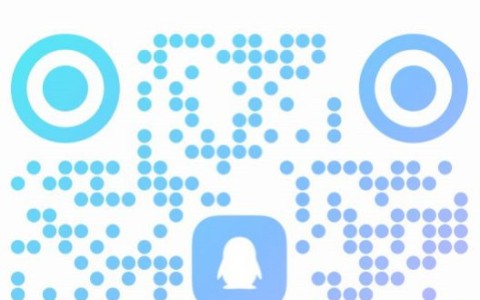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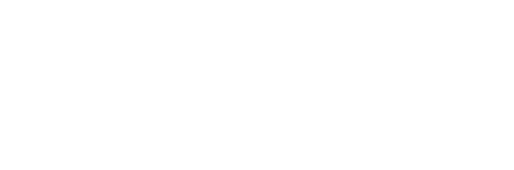
评论列表(3条)
我是葡萄号的签约作者“沛芹”
本文概览:古代医德名言篇(一) 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黄帝内经》 论曰: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
文章不错《古代医德名言》内容很有帮助